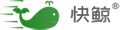帮G管理,给B赚钱,为C服务。
作者 | 王与桐
编辑 | 火柴Q
趋势与洞见No.71近日,高仿版出入证出现在北京市天通苑社区。
李逵和李鬼
有点可笑,有点可悲。天通苑作为亚洲最大的常住人口近50万的社区,在疫情中仍采用与非典时期无异的纯人工管理模式,带来隐患。
这是我国防疫过程中数百万尚未信息化的社区的缩影。不智能的社区是相似的:
一些政府部门仍然需要打电话来掌握患者数字的变化;居民需要亲自到居委会/物业办公室领取纸质通行证;虽然社区关闭,但温度测量取决于人,注册取决于纸和笔,所有居民共用几支笔;虽然一些社区安排了守门员,但他们没有询问体温的来源,这是徒劳的;为了外防输入,社区进出时需要密码,这也是微博上的热门搜索。
小区暗号热搜
纯人工管理模式靠嘴、靠腿、靠经验,不仅人工成本高,管理难度大,还可能增加感染风险。
智慧社区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力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成果之一。
疫情前,高智慧城市订单屡见不鲜:
2019年7月,腾讯云以5.2019年9月,阿里4022万中标雄安BIM管理平台,这只是阿里巴巴自2017年以来为雄安建设城市大脑的一部分。不仅是大城市和新区,三、四级城市也接近智慧城市。例如,2018年广西玉林市招标的智慧城市(一期)项目总投资约为8个.2017年,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作为县级行政单位,也公布了总投资10亿元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副省级城市100%、地级以上城市89%、县级城市49%已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参与地级城市300多个,规划投资3万亿元,建设投资6000亿元。
智能社区一直是这些总额惊人的新基础设施项目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为例,其智能社区约占智能城市总发展指数的10%~20%。
从以往的报告来看,中国信通院发布的 智慧城市建设成果非常美丽** 显示,2019年我国大部分省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超过0.其中,湖北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十。
但猝不及防的疫情给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泼了卸妆水:
一方面是建设上的大投入,另一方面是执行上的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了AI辅助决策等高端智慧,即使是口罩预订、体温检测、信息报告、审批文件等可信息化、在线的行政事务,仍以线下人工处理为主。
经过几年的巨大投资,社区仍然不够聪明。问题是什么?

*严格来说,社区是公共管理的概念,社区是商业的概念。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将公共管理概念的社区和商业概念的社区统称为社区;由于我国智慧城市边界模糊,智慧社区归口不同,本文将信息化、智能化社区统称为智慧社区,便于描述。
1.谁是局中人为什么社区要走向智慧?有三个目的——帮助G(政府)管理,给B(企业)赚钱,为C(人民)服务。
政府想要既高效又能与物业、业主沟通的监管平台;物业公司想要移动化的智慧物业管理平台,降本、增效和创收;科技公司等建设者想要落地场景,以打磨技术和带来收入;业主和居民想要全新的移动化社区生活服务平台。
事实上,疫情中的许多实践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智慧社区参与者的角色和作用。
一是政府,它是智慧城市的客户,也是领导者,掌握政策、规划和资金。

不同层次的政府有不同的决策权。中央政府是统一的决策者,负责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总体规划;市/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责任水平** 极高;街道办事处是城市最小的政府级别,主要功能是承上启下。
社区是与居民生活最相关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的主体。社区虽然属于居民自治范畴,但实际上是街道办事处管辖的。
智能社区的设备和系统可以由区/市政府统一采购,然后在社区实施;采购事宜也可以由社区独立决定,但需要经街道办事处批准才能获得财政拨款。
以有1.以上海浦东联阳社区6万户人口约5万人口为例,其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需要通知200个口罩,接受2000多个口罩的预约需求,工作量超负荷。2020年1月底,社区开始购买呼叫机器人,最终使用了一个小家庭i机器人防疫外呼机器人产品。采购是免费的,不涉及财务申报和审批程序,但仍与上级签订相关协议。
疫情期间,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利用陈安科技提供的应急数据平台,为辖区内47个社区和487个社区服务,自动收集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分析结果将转移到区/市政府系统。此时,政府是决策者,社区是执行者。
然后是科技公司,是智慧社区的具体建设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集成商和新集成商,包括神州数码等系统集成商,中国电信等运营商以及平安、阿里、腾讯和华为在内的巨头型解决方案商;他们负责拿下整个大单,其中的许多工作会分给合作伙伴。
另一种是从爱物管、城云科技、竹间智能、陈安科技、卢深视等细分轨道入手的科技公司。他们可以集成,也可以选择独自为政府和社区服务。
最后,物业公司是智慧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可以是甲方或乙方。
政府希望当地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公司负责管理社区,即智能房地产和房地产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的房地产公司是政府的乙方,需要服从街道管理;但房地产公司一般缺乏独立的技术能力,也是购买信息、智能设备和系统的主体,是甲方的科技公司。
参与者众多,目的、能力和合作程度各不相同,使得在萌芽状态下建设智慧社区更加困难。
疫情来临时,缺陷暴露。
2. 孤岛丛生,青黄不接在产业链各方角色的行为逻辑中,智慧社区仍然不智慧。
首先,从智能社区最大的领导者和政府支付者的角度来看,智能社区的缺乏发展首先与中国政府信息化本身起步较晚有关,作为政府周边的社区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
AI物业管理平台爱物管CEO滕一帆告诉「甲子光年」:中国可能只有不到1%的社区完成了基本信息化。
社区信息渗透率低,与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重点有关。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包括交通、公共安全、消防、健康环保等方面。地方政府将根据当地发展情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相应的预算也有所不同。
例如,山东济南在交通大脑上投入了大量资源。第一阶段的建设投资超过2亿元,智能信号灯在334个十字路口上线;三亚与华为、尚堂、平安等科技公司合作,重点建设智能旅游项目。这些城市的战略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优先解决关键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欢告诉我「甲子光年」: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余力服务民生,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财政实力差的地区会把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上,无力服务民生。
其次,除了信息基础薄弱外,中国智能城市和智能社区的建设也受到数据岛的困扰
数据岛有三个原因:一是各职能系统本身之间的部门差距;二是中国政府创新模式在全国推广前进行地方试点;三是受规划者思维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IT在叠屋架床多年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孤岛。
先说各系统之前的部门隔阂,造成了条状孤岛。
在中国,一些功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例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 ** 等部门也有自己的系统,纵向信息可以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受阻。
块状孤岛是由中央牵引规范的创新模式引起的。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正处于探索时期,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在成功经验后指导推广,而不是强硬的决策。例如,大众公共安全防治项目雪亮项目是在山东临沂首次尝试并取得成功后,于2017年6月由中央政府向全国推广。但这将带来扫雪的问题,导致地区划分的数据岛,地方数据不交换。
以上两个原因可以概括为缺乏顶层设计——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权责划分还不够明确。
上海、深圳、重庆等,如上海、深圳和重庆,已经建立了智慧城市规划机构,但更多的地区仍然是混乱的——以智慧社区为例,有综合管理办公室管理,有政治和法律委员会负责,但也与公安部门有关——谁听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
何野,重庆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甲子光年」它讲述了重庆市政府在智慧城市领域的权力变化:2013年,重庆被国家批准为智慧城市试点项目。当时,相关项目由市政府牵头,国土规划、经济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等部门共同领导,但进展不令人满意。2015年,重庆成立了市规划局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突破了医疗、交通、政府事务等领域,智慧城市建设逐步走上正轨。
可见,要建设包括智慧社区在内的智慧城市,首先要设计好顶层结构,这也是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
最后,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早期阶段,许多地方喜欢叠加大量的硬件和技术,导致许多地方在岛上重建岛屿。延伸到社区小单位,这种复杂的现象更为明显。
爱物管滕一帆认为,包括疫情在内,一些地区已经紧急开发了大量的系统,连接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系统和数据是独立于原有系统的,仍然无法相容,相当于建造了一批新的孤岛。
不难理解为什么现有的建设在疫情突然来临时并没有迅速显示出足够的应对能力——因为疫情防控所需的综合数据无法有效流通,很难快速与其他基层系统共享。
疫情过后,未来可能会闲置一些应急系统和设施,造成资源浪费。
看看智能社区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特定项目的建设者和科技公司。
总的来说,从供给侧来看,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的效果并不理想,两代建设者仍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第一代建设者是神州数码、东华软件、浪潮软件等集成商和中国电信等运营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兄弟”——大量软件外包公司。
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一阶段的主题是信息化。其目的不是实现城市的真正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而是实现在线化。
但由于上述地方政府资源与执政重点的差异,这一步工作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市之间参差不齐,导致许多城市的在线政府管理水平较低。
典型案例之一是武汉与微软签署的1.智慧城市烂尾项目75亿元。
该项目于2013年12月正式签署。当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微软及其授权的华盛天成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在智能城市项目等六个方面开展战略合作。这涉及9个角色,如下图所示:
整整三年后的2016年底,武汉方对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最终实际效果与微软之前的承诺有很大差距,属于不合格产品Azure公共云的利用率只有12%,信息化几乎没有实现。
2016年,杭州推出了城市大脑理念,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其特点是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从这个阶段开始,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华为等科技实力雄厚的跨境玩家开始进入智慧城市to G大市场,并逐渐为新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新的集成商。
客观地说,智慧城市的第二阶段只有三年,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智慧城市建设周期长,各种新技术方案仍在成熟,其投资建设效果尚未充分显现。
然而,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前半部分,即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从2010年到2017年,中国视频监控市场规模从242亿元增长到1142亿元,复合增长率超过24%,进一步扩大了海康、大华、宇视等安全企业的规模,第一批视觉人工智能企业获得了较高的估值。
然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不能完全解决后半部分的执行问题。在管理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做线下工作。
疫情中某二线城市某街道办事处的一个案例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特点。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张雨告诉我「甲子光年」,他们的一个社区有一个大广场,通常有很多老人聚集在一起。2月13日,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从监控摄像头上发现,广场上聚集了20多名老人。当时全市新冠肺炎病例525例,当天新增7例,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虽然这个信息及时传到了社区,但是社区没有有效的通知和无人管理手段,只能派两个人留在广场上劝老人回来。
有裂缝的地方有光进来的可能,to G信息化智能市场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
3.疫情 ** 玩家换代疫情暴露的智慧城市问题可能会促进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迭代,投射到to G在大市场上,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加快智慧城市相关玩家的升级,包括智慧社区。
传统集成商或是有国资背景,或是国际巨头,或是已成立几十年,他们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是更值得政府信任的合作对象。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应该为智慧城市服务的建设,集成商需要满足政府信任之外更多的条件:AI和云计算等高科技能力、作为核心资产的数据、海量场景、资本优势、生态能力——这些给了“新集成商“上场的机会。
“在政策和市场的催生下,以平安、阿里、腾讯、华为为代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开启了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之路。”平安国际智慧城市商务管理部总经理曹晓兵这样评价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格局。
科技巨头之外,包括商汤、依图、特斯联和云天励飞等乘AI浪潮崛起的成长期科技公司也获得了机会。
近年来,新集成商的to G订单数量大增,并带来了产业生态的急速扩张。
截止2019年,在智慧城市领域,阿里和超过2000家企业保持合作关系,为全球23个城市引入城市大脑;华为有1100多家合作伙伴,为全球200多个城市提供智慧城市服务;腾讯与150多个城市建立合作,其中智慧交通已经在全国300多个城市落地;平安智慧城市建设覆盖了全国110个城市……“新”玩家们势头迅猛,快速做起更大的蛋糕并开始瓜分。
老玩家们,要么被取代,要么主动变革。
而本次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和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教育”在疫情推动下或将前进一大步。智慧社区3D视觉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卢深视CEO户磊告诉「甲子光年」,有多种信息预兆,疫情深刻教训下,不少省市的相关部门已开始做智能化的规划设计。
而无法实现智能化管理的各地政府,会对合作的集成商提出新的要求,甚至会考虑与其他大公司合作。这是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好契机。
4.“补漏”指南在承建者整体向智能化倾斜的前提下,本次疫情前后的各种动向,也在指示着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些方向。
一是,钱在从三四线城市流向大都市圈。
这里的钱是指中央财政。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明确表明,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建设等“新基建”的重点将向大都市圈、城市群转移,与人口流动方向相适应。
但钱扎堆的地方不一定就意味着有肉吃。大城市有更多资源,也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对初创科技公司来说,如难以获得大城市的入场门票,则要抱大腿——融入巨头生态,或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做好细分市场。
智慧社区作为智慧城市大蛋糕中的一个热点细分领域,在商业模式上也有一些特殊玩法——对普通社区来说,一次投入几十万建设智慧社区非常困难,因此目前市场上比较流行以社区广告位的形式抵款。
这其中的机会在于,可以构建一手做智慧社区,一手开拓增值服务的模式;而这个模式的难点是找到一个可在较多社区间 ** 的切入点,因为不同社区的需求各不相同,且服务社区时还需要接受业委会、街道办的限制。这个细分领域的竞争,实际上比的就是提炼出相对通用的需求,并不断打磨、迭代和 ** 的节奏感。
二是,政府从顶层设计层面,会更加意识到打破数据孤岛的必要性,这将为政务数据分析平台领域创造更多机会。
在这次疫情中,浙江省不仅借助阿里的城市大脑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数据,还实现了政务数据和阿里、携程等公司提供的商业大数据联动,形成了从微观收集到宏观分析的管理闭环。城市互联网运营商城云科技高级副总裁沈瑶告诉「甲子光年」,仅是政务数据的打通,在国内很多地区就无法做到。
“打破信息孤岛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平安智慧城市曹晓兵认为,这次疫情,会逼着各地让信息数据流动起来,然后加快公开透明化。
三是,从感知自动化到治理自动化的全链条打通,巩固“前一半”,走完“后一半”,这将为物联网和智能设备领域带来机会。
在巩固前一半,即数据的收集和流转上,仍有大量薄弱环节有待加强。这也是物业公司目前布局的重点。
如华润置地写字楼在此次疫情中采购了数百万订单的红外线测温仪,在其写字楼和联合办公空间投入使用。除了具有测温功能,该测温仪还可以实现将体温异常数据流转至监控中心,并由AI技术提供分析检测报表。这一功能并不复杂,却大大提高了测温的效率。
走完后一半,则对应上文提及的,目前很多智慧城市只解决了前一半“感知”问题,即在采集和分析数据上有进步,但到了具体治理措施的落地,仍存在大量低效的线下工作。
从这个“漏洞”出发,可以预判,未来的智慧城市建设将借助更多IoT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接入更多智能设备。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平安在全国各地的社区紧急投放了一千多个和商场迷你KTV一样大的小问诊间。“其实就是把平安好医生线下化了,”平安国际智慧城市曹晓兵告诉「甲子光年」,问诊间里有人脸识别设备和健康检测设备,还有远程医生“坐诊”。如果居民身体有异常,不用出小区就能看病。
长远来看,由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更深入的“治理自动化”是解决政府部门人力不足的必由出路。
最后,值得注意的大背景是,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已走上独特路径,已没有“先进案例”可参考。
对整体上强于模仿,弱于创新的中国,最大的范式转换就是要开始深刻体悟创新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在实操上做好预案,在心态上给予包容。
唯有如此,下一次突发事件来临时,小区对暗号的“敌后武装队”剧情才会成为历史。
END.
扫码咨询与免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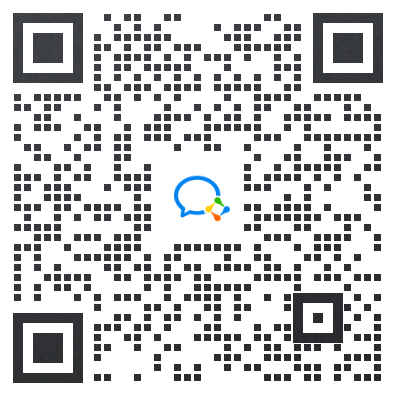
申请免费使用